艺术家常常以固定的形象和面目为人们所接受,但那往往只是一种“表面”和“假象”。梁楷是南宋宁宗时期的画院待诏,皇帝曾经特别赐他金带,据说梁楷在面对这一至高的荣誉时并未接受,而是把金带挂在院中,自己飘然而去。这个故事真实与否尚有争议,但却非常符合读者的心理,故事中梁楷这种“有所不为”、淡泊名利的狷者形象,寄托着“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”,也勾起人们对于如孔子、关羽、李白等古代圣哲的追忆。因此,与他细密精工的八高僧故事图卷相比,《泼墨仙人图》和《李白行吟图》这样的简笔作品在人们心目中更能代表梁楷的画风。
《泼墨仙人图》也许只是梁楷一时兴到偶然所作,率性、潇洒中甚至透出一些醉意,全图以大笔涂抹,只在脸部略作勾描,画出紧密攒聚在一起的双眼鼻口。仙人的形态很明显是对正常人相貌的一种夸张,更可能是梁楷对自己内心的写照,细看之下,又觉得每一笔并不那样随意,甚至像是早有“预谋”的抒写,当然这些全都建立在他能够精准熟练掌握画技的基础之上。有意思的是,画面上除了仙人形象和一个穷款之外,梁楷并没有过多地表述他创作这幅画的目的以及时间地点等背景,这留给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,也增添了绘画的阐释可能。然而多事的乾隆皇帝为它题写了一首绝句,试图为此画提供权威性的注解:“地行不识名和姓,大似高阳一酒徒。应是琼台仙宴罢,淋漓襟袖尚模糊。”不仅如此,皇帝还利用他的号召力,组织臣子同他一起观赏画作并——题和,以使他的“注”派生出众多的“疏”来。
与《泼墨仙人图》命运相乖的是,梁楷另外两件人物作品《斫竹》和《撕经》流传到日本,画面至今仍保持着最初的样貌,从未经人题写——这令人难以理解地形成一种矛盾,《泼墨仙人图》因为大量的题诗而丧失了本有的诗意和“光晕”,而《斫竹》和《撕经》却因为没能得到题诗或者“笺注”显得更加意味深长、富于“禅意”。《斫竹》和《撕经》像是一组作品,画中的人物被认为是六祖。不过,《斫竹》和《撕经》的隐喻却是可以推究的:斫竹人砍去竹竿上的侧枝,让它成为一种有用的物件,这让人想到儒家的“格物”,而撕经者的打扮更像是一名道士,他将经卷——或言书本用手扯碎,可能表明的是已经悟道的他不再需要这些求道的工具和媒介,也可能是认为文字、知识是一种障碍,它们会妨碍自己对“道”的认知和体悟,因此应当“破”之。《斫竹》和《撕经》就像是关于“证道”的两种寓言图像,一正一反,一种是积极的传统的渐进的,一种是逆向的反动的顿得的,它们为文人画的“性情”注入了“思想”——不论这种思想是产生于创作机制还是接受环节。
如果说梁楷的人物画是一种“禅的诗学”,那么牧溪的山水画便可认作是一种“诗的禅学”。牧溪的作品是否可以被归为文人画一直以来仍是备受争议,批评者责怪他的画“粗恶无古法”“诚非雅玩”。我深深觉得这种苛责是过分的,牧溪的画实际并不“粗恶”,甚至有非常细致写实的精心之作;所谓“古法”的概念也是相对的,牧溪的确有一种现代感,但它并不意味着背叛,而是通过做“减法”来引领时代的“潮流”——“简”或许才是真正的“古法”,是对“古”的回归。牧溪对水墨的掌握非常熟练,也特别乐意为笔下描摹的对象留出“意义”层面的空间,试图通过营造“朦胧”和“清幽”的水墨世界以消解“性情”,正因为这样,牧溪的画与那些致力于“抒情”的文人画有所区别,它不是基于性情的、不是绮错的、不是抒泄的,但这种最本然的状态却能调动起人们的感发,就像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里总结的那样:“岁有其物,物有其容;情以物迁,辞以情发”,牧溪的画就是引人发自然之感和文学想象的触媒,是关于诗学的禅,因此,在本土并不受到青睐的牧溪及其作品被追求“物哀”与“幽玄”的日本人奉为瑰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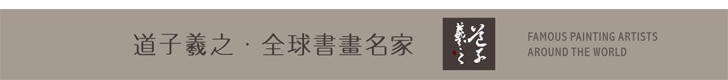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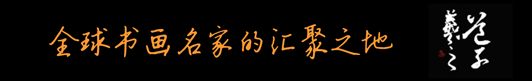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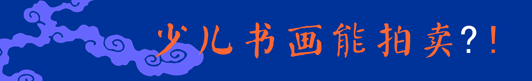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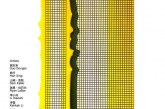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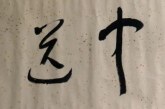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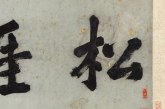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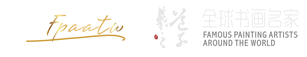
 新公网安备 65010402000864号
新公网安备 65010402000864号